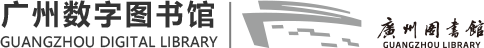张振金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教授。40多年前,18岁的他在暨南大学读中文系,业余时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同学们一起去攀登白云山。“我们三五成群,从暨大踩单车一路行进到白云山北门一带,然后兴高采烈地上山。”
.jpg)
梁俨然和他写的关于白云山的书
那时候的白云山路很不好走,上山下山要用去一整天的时间。虽然如此,白云山如画的风景却让这些年轻人流连忘返。张振金印象里最深刻的,是白云山上大大小小的瀑布,九龙泉、蒲涧濂泉以及知名不知名的泉水,飞流直下,清凉的水滴溅到脸上,让人感觉无比清凉。
半部岭南文化史
一开始是被美景所吸引,再后来就在白云山里发现了许多当时还稍显荒凉的遗迹,能仁寺的断壁残垣,云岩上古老的石刻,百花冢里的暗香……张振金开始对白云山上的文化记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一头钻进了故纸堆里,展开了研究。
“白云山是座有文化的山。它不同于罗浮山是道教圣地,也不同于丹霞山因为佛教而出名,白云山是以历代文化名人的聚会而出名的。”
.jpg)
百年前的白云山暮鼓晨钟此起彼伏。
“曾经有人感叹岭南文化积淀不深,可是如果你了解了白云山的历史,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这么说,半部岭南文化史要从白云山说起。”
诗人吟咏之地
张振金说,早在2000年前,白云山就已经开始自己的文化历程。
唐宋时期的白云山,文化氛围之浓,绝不亚于庐山、泰山等全国名山。那个时候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善恶、爱国与卖国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许多忠直贤明的人都被贬到当时属荒蛮之地的广东。这些贬官之中,有许多都是当时著名的诗人,虽然能诗善文,又贤明正直,可是却郁结在心,不吐不快。自然而然,白云山就成了他们足迹所至地。
曾经乱石险峻
最先走上白云山的是杜审言,他是和另外三位初唐时期著名的诗人沈佺期、宋之问、张说一起贬来的。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他的五言诗写得极其出色。他来到广州的时候,白云山还不叫白云山,而叫“乱石山”,杜审言笔下的白云山乱石险峻诡谲:“上耸忽如飞,下临仍无地”,景色变化无常,“潮燉赤丹紫,夜魄炯青翠”,鸟兽神秘繁多,“万寻挂鹤巢,千丈垂猿臂”,杜审言“观此得咏歌”,而且使他离去后“长时想精异”。
风景秀美
文人汇聚
元代是白云山文化的沉寂时期。因为广东是抗元活动激烈的地区,白云山也受到严重的损害。到了明清才逐渐恢复。
清嘉庆17年,岭南七位诗人黄培芳、张维屏、黄乔松、谭敬昭、林伯桐、梁佩兰等集资,在白云山濂泉坑外谷口处,兴建云泉山馆,这里是清代广州文人聚会之处,名曰“七子论坛”。
既然是诗人学士常常吟咏的地点,云泉山馆必有其独到的景致,黄乔松写过一首《穿云径》,诗曰:“人行云亦行,人住云亦住。杳然不见人,但见云来去。盘旋入层云,人声落空翠。”据说当年云泉山馆有24景之胜,穿云径只是其中之一。
历代文人为何如此重视白云山呢?张振金说,白云山不像众多名山那样有沉郁的宗教氛围,文人们来此并不是寻找精神的皈依点。所以,吸引他们的是自然风景的秀美。
正像一首音乐有高潮部分,一首诗歌有点睛之笔,白云山在平原拔起,常常有山势极为陡峭的悬崖,白云山由此天然地具备了许多瞭望平台,所谓“白云晚望”、“白云珠海”、“锦绣南天”皆由此而起。
古人有诗云:“一峰高耸万峰巅,满目云烟紫翠连。”其实,白云山就是这样万峰簇拥一峰,云烟连缀紫翠,从而形成它的整体美。“白云山就像一部综合的文艺作品,有油画的博大深厚,有剪影的灵巧明丽,有长诗的磅礴气势,又有小说的幽深奇谲。”
深厚文化积淀
张振金说,得到历代文人学士厚爱的白云山,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化是一座山的灵气和神韵。不管哪座山哪道水,要是缺少了文化,虽然山还在水还在,但它的灵气和神韵就马上消失。
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里的“仙”和“龙”,其实是一种文化现象。如果琅琊山少了醉翁亭,西湖缺少了苏堤和白堤,洞庭湖缺少了岳阳楼,那情景将会怎样呢?山水因为文化而增辉,文化以山水而添色,二者融为一体,才使得中国名山胜水形神兼备。
.jpg)
白云山能仁寺里的一条金龙。
“一开始,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1938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广州,还要不断地把炸弹投向白云山,把汽油的烈焰倾向白云山。原先绿阴如盖的白云山从那个时候变成了一座秃山,连一座座岩石也炸成了粉末。能仁寺毁了,白云寺毁了,濂泉寺毁了,云岩寺毁了,双溪寺毁了,月溪祠毁了,景泰寺也毁了……
今天的白云山,在后来人辛勤的耕耘下,重新绿阴如盖。张振金说,和他最初记忆里的白云山相比,今天的白云山树多了,路变得好走了。
不过,更让他心驰神往的,还是那对景当歌的浪漫年代。
梁俨然:白云山诗翁
今年已经九十多岁的梁俨然老人有个称号,叫“白云山诗翁”。他这辈子写了数不清的诗歌,其中很大一部分和广州白云山有关,它们被辑成《白云山诗稿》传世,这在广州诗界是独一无二的。
“郑仙诞”热闹非凡
梁老笑眯眯地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此生与两座‘山’有缘,一座是广东鹤山——那是我的祖籍,另外一座就是广州的白云山。”
梁老告诉我们,他自小生活在广州的西关,几乎是从有记忆开始,就知道广州有座好美好美的山——白云山。
白云山最热闹的日子叫“鳌头会”,又叫“郑仙诞”。传说中的郑安期于7月25日采仙蒲驾鹤而去,千古年来的广州人认为,在这一天上白云山采菖蒲、沐灵泉、祈夙愿,就可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jpg)
白云古寺遗址。
梁老告诉我们,虽然郑仙诞是在农历的七月二十五,但是老广州通常在农历七月二十四晚上吃完晚饭就开始上山了。爬到白云山山顶待上一个晚上,第二天祈福完之后再下山回家。
那个时候,梁老还是个小孩子,他记得鳌头会游山之日盛况非常。时人有“满天花雨湿罗衫,纷纷游侣出城东”的说法。
过去的白云山还没有今天这样宽阔的马路,上山只能由小北门到山脚白云仙馆过姑嫂坟、长腰岭,登百步梯将军岭,从能仁寺的背后上到郑仙岩和郑仙庙,或者是从沙河乘马车到濂泉下车,然后上九曲濂涧,沿百步磴、观翠岩、舍身石一路到郑仙庙。
在梁老的记忆里,每到郑仙诞,广州城的老老少少相继出城东北门,络绎于途。山路两旁摊档密布,茶水档、饼食档、花卉档、纸花档、风车档、摇鼓档、香烛档……太阳下山时,从山脚往山上望,可以看到灯火相连,仿佛一条闪闪的“银链”挂在白云山上。
山清水秀白云山
现在的白云山很美,可是梁老认为,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白云山更美!
用梁老的话来说,那个时候的白云山可以用“清秀”二字来形容。在山中徜徉,不知在哪个拐弯处,就可以和一眼灵动的泉水不期而遇,它们有的纤细婉约,有的喷薄如瀑布,各有各的好看。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蒲涧濂泉。那个时候的蒲涧濂泉水非常大,梁老和自己的小伙伴可以在里面游泳,至今回忆起来,似乎都能重温浸润在濂泉那又清又凉的泉水中的畅快感觉。
.jpg)
在双溪古寺遗址上建的双溪别墅。
抗战八年是白云山最惨淡的日子。梁老说,那段时期白云山上的树和庙宇都被人给拆光了,整座山变成了秃山,老广州把它叫做“童山”。建国之后,广州人开始在白云山上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现在这些树林都长大了,白云山的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茂盛。
百回鸿印百回诗
上世纪50年代,梁老居住在西关一所古旧而昏暗的房舍,他给房子起名为“墨屋”。由于常常渴望阳光,羡慕青山绿水,所以来白云山的次数就更频繁了。
在探寻白云山的古迹和遗事的过程中,他接触到许多前人吟咏白云山的诗句,本身就是文字工作者的他,也忍不住开始吟诗抒情。后来,他几乎每爬一次白云山,就会作几首诗,不知不觉中就累计有300篇之多了。第一百回游白云山的时候,梁老写了这样一首诗:人生汗漫几多时,绿水青山不自知。吟到白云无尽处,百回鸿印百回诗。
《白云山诗稿》在1996年出版。刘逸生老先生为之作序。序中这样说:白云山乃广州名山。广州偌大一个城市,钟情斯山者,不计其数。然似“梁子之特嗜也”者,则绝无仅有。梁老“于斯山最有情”,以至“书帷灯幌,朝晖夕阴,无不见白云也;涧溜松声,履痕梦影,无不有白云也;呼朋啸徒,消寒拂暑,又无不趋白云也。”
诗人纷至沓来
到了宋代,苏东坡、刘克庄、方信儒、杨万里以及广州本地的白玉蟾、李昂英等著名诗人纷至沓来。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苏东坡。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继被贬黄州之后,又被贬到更药园荒蛮的广东惠州。他在4月离开京都,6月途经南京,9月跨越大庾岭。苏东坡在广州的白云山一共留下四首诗,《广州蒲涧寺》里他说:“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他竟然连个向导都不需要,是自己寻着泉水来到这里的。
.jpg)
白云山上陶铸及其夫人的墓碑。
苏东坡是宋代第一个被贬到岭南来的官员,这个时候的他已经58岁,命运的荣枯盛衰、起落浮沉已经历了不少。虽是被贬而来,苏东坡却是无忧无惧,心中一片宁静。他和白云山的僧人关系亲密,既无大诗人之威,也无谪者之忧。《赠蒲涧长老》里,他说“宴坐林间时有虎,高眠粥后不闻鸦。”《发广州》也表现了苏东坡怡然自乐的心态,他不仅“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而且“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樵渔。”
张振金发现了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我在图书馆查阅了许多资料,那么多和白云山有关的诗歌,每一首都是快乐的,没有一首有忧伤的情绪,哪怕它们的作者,大都是像苏东坡这样,被贬岭南,正在度过他们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光。”
也许,这就是白云山的魅力所在。
撰文 金叶
摄影 黎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