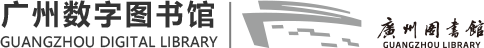.jpg)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25年从欧美留学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52年起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发表的学术论文近百篇,专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1)、《元白诗笺证稿》(1950)、《柳如是别传》(1965)等。
国学大师陈寅恪从年轻时就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私家藏书楼到世界各国图书馆,他一直游刃自如地读书用书,即使老年失明,仍能凭记忆通过目录请助手帮助参阅图书。
在私家藏书楼打下国学基础
老一辈学人,多数开始都是靠家藏的图书和由此而来的私家藏书楼获得知识的。而私家藏书楼,通常也就是包括陈寅恪在内的前辈学者,最早接触到的图书馆。
陈寅恪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晚清出现的大学者、大诗人。两代人在家乡江西义宁(修水)经营起自己的藏书楼。年轻的陈寅恪由日本归国后的十几年里,日日夜夜埋头于藏书楼,苦读父辈所庋藏的经史子集和佛经,无师自通,就此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读书破万卷,正如后来王季思(王起)教授所说:陈寅恪先生所以能有巨大建树,原因之一,就是善于掌握丰富的图书资料。他的表弟、同学多年的俞大维也说:“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必求正解。”
好读书,也求甚解。案上书要少,心中书要多。陈寅恪在私家图书楼受益匪浅,若干年后,当他回顾这段生涯,对所读书籍如数家珍,一一评论:
“无论你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周礼》是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的书,不论其真伪,则不可不研读。”“《仪礼》,礼和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于礼的根本,则终不可废。”“《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适合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都为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远在世界上,也是最精彩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懂,且须要背诵。”“《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的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
瀚海披沙,飞珠溅玉。这也是一位通儒在向经典古籍的读者做点睛式的读书指导呢。
陈寅恪在藏书楼做学问是出了名的。1917年,他在首次留学欧洲归来在南京憩息时,当时京师图书馆就已发出聘书任他为图书馆主任,但因已计划再度赴欧留学而作罢。
在图书馆度过欧美大学生涯
陈寅恪是从私家图书楼走进世界图书馆的。早在1909年,19岁的陈寅恪靠公费资助,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后又到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读书。1914年回国,1919年转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希腊文和巴利文。1921年,离美再赴德国,在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学。在不长岁月里,竟读了多个大学。要读完这些大学,按常规非得要二三十年不可,但他却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
那是因为他每进一所学府,往往仅花一年半载,有时虽在课堂,但更多时间和精力是放在经导师辅导到图书馆读书和在图书馆自修,在较短时间把要读的全部课程进修完毕。故不需再等到学制结束,就另觅新校了。他的欧美大学生涯,几乎就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因而,他的一生没有一张大学毕业文凭,逞论学士和硕士、博士学位。以至1925年回国,梁启超推荐他去清华国学院做导师,当局竟以连一张文凭都没有拒绝接受呢。
陈寅恪在国外更多的时间都是去图书馆。他在柏林大学研究院时,因为国内经费来源终止,为节省开支,每天清晨购置廉价面包,躲进图书馆度过一整天,废寝忘食。甚至常因连廉价面包都买不起,而放弃午餐,继续看书、查卡片、摘录资料。
他在各大学图书馆博览群书,而有两种图书备受他青睐,一是语言文字书,一是宗教书。陈寅恪还特别喜欢找这个方向的罕见书阅读。在柏林期间,有次他在图书馆读卡鲁斯《古英语文法》,同学毛子水感到诧异:为什么费工夫读这样一部老书?他却回答说:正因为它老的缘故呢。这大概是一则老书传世,说明经得起考验,值得一读;二则老书找得不易,要珍惜机会。他读宗教书,倾向于佛学方向。由于熟悉梵文、巴利文、藏文和蒙文等,所以他常在图书馆借得多种文字的佛经古版本做校勘、考订,从比较中发现古中国人以汉文译佛经时的不少问题。他说:“我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至清末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为常跑图书馆,查书读书做研究,陈寅恪也习惯于不断编制新书目(篇目),充实并完备自己已有的书目,按图索骥。近年发现他20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在德国留学时所做的64册札记,从中可以蠡测他图书馆生涯的部分记录,也可窥出他对书目学的关切。
据季羡林教授介绍,这些札记涉及蒙、藏、突厥、回鹘、吐火罗、西夏、满和朝鲜等多种文字,以及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和希伯来文;内容涉及佛经、哲学、兵法和小说等,其中不少本本就抄有书目。因此季羡林整理这些札记后,大有感触地说:“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二十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
结缘敦煌学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时,讲授课程范围甚广,但几都是自辟蹊径的创举,其中就有一门“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佛经翻译文学”(图书介绍)。每当讲授有关佛学课程时,则用黄布包包着有关参考书上讲台。又因为他熟悉中西文化和佛学,研究院图书馆凡采购外文书刊和佛学典籍,都得经他最后审定。
在此前后,陈寅恪充分利用海内外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做研究,并解决了很多疑难,其中有些可以说是常识,却因过去治学者不够严谨而犯下的低级错误。如晚唐诗人韦庄长诗《秦妇吟》原刊本有“一斗黄金一斗粟”句。他以早年在巴黎图书馆阅读的相关敦煌卷子中皆写作“胜(升)粟”为证,得出正确结论——应做“升粟”。盖古人书写潦草,后人不察,有误识“升”为“斗”字,如三国刘禅小名“升之”(阿升),误做“阿斗”,讹传百年也。
陈寅恪对于敦煌卷子的兴趣,在回国后仍意犹未尽,又多次从北京图书馆查阅庋藏残存的敦煌卷子。他此时所写的《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就是从俄、德、日等所藏的八种文本《金光明经》考证,说明它流传之广,“以其义主忏悔,最易动人故也”。而《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也是从所藏的敦煌写本的考证,有力地提供了佛教进入中国被改造、被消化的一个样本。
三十年代初,他在北平,常与陈垣教授切磋学问,两人志同道合,有时就《元朝秘史》等诸家版本商讨,有时也切磋目录学。当时陈垣教授将庋藏于北京图书馆所剩余敦煌卷子八千余卷轴目录编为《敦煌劫余录》,陈寅恪大有兴趣,特地赴图书馆仔细读了,并从九个方面为这些卷子编目,以突出其重要的文化价值。且还在序文里,首次提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向图书馆读者介绍这门新学科。
读常见书,写名山大作
陈寅恪童年时代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有人说他读了多遍二十四史。与许多人读史注重传记不同,他尤注重各史中的志书。他推崇《资治通鉴》,将它作为备课的起点,并以此文书与其他史书做对照、比较、鉴别,以此为本,对它们的文化价值作出判断。因为读书万卷,陈寅恪治学往往从图书馆里常有的史书中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提出符合科学规律的见解,破译千百年里沉淀的密码。抗战时期,他在香港讲演《武曌与佛教》,所据的材料就是从本地一家不知名的图书馆找来的《隋书》和新旧《唐书》以及《续高僧传》。1943年春,在桂林期间,也是从广西大学图书馆因阅读日本《东方学报》等书刊论文中有关于唐朝租庸调制的研究,颇有感触。即从新旧《唐书》和元稹、白居易的《长庆集》等几部图书馆常备的书中引申、考信,而写出名山大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
.jpg)
陈寅恪晚年在广东中山大学教学20年,着意研究的是“柳如是”。早在三十年代,他就酝酿这个课题。在上海还多次赴合众图书馆查阅钱谦益文集和钱曾的《牧斋诗注》;五十年代后,因为双目失明,写作只能口述参考书目,提示助手和他人帮助查书。据中山大学周连宽教授回忆:“我曾协助他做资料收集工作,前后已十年之久。他每天把所想到的问题若干条记录下来,交给我去图书馆查找有关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作者在这部有8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里,旁征博引各种典籍多达600余种。其中诗文集(包括宝卷、弹词)约240种,史书、年谱约170种,方志约50种,如果包括听过(助手根据书目借来的书刊念给他听)而未引用或稍作参考的书刊,当有千种。这些书极大多数仍是一般学者常见常用且常易找到的图书馆藏书,很少有善本、珍本或海内孤本。这都是他在双目失明、行动极不方便的特殊处境中,利用图书馆和发挥自己目录学所长的成果。
.jpg)
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的故居
.jpg)
.jpg)
陈寅恪生前在中山大学
图书馆打造了大师,大师也增辉了图书馆。“文革”时期,陈寅恪屡遭迫害,含恨而逝。后来,他的家属将其在广州所藏的全部图书,赠与曾任教的中山大学图书馆。十年后,中山大学特辟定陈寅恪纪念室,以激励后学,永远铭记这位国学大师,纪念他与图书馆的情缘。
上一条: 郁达夫:读图书馆最勤奋的一个作家
下一条: 史量才:中国流通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