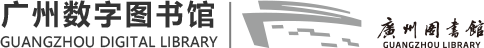岭南大学
1844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博士和香便文博士商议筹办一所高等学校,决定校名为格致书院,校址最初在今广州六二三路,1888年正式开课,1903年更名为岭南学堂,由澳门迁回广州河南康乐村。1906年后,岭南学堂改称岭南大学,并最早实行男女学生同校。
.gif)
1927年,岭南大学改由华人自办,仍接受教会资助(美国教会设立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首位华人校长是钟荣光,他是岭大的第7位校长。陈序经为第9位校长。陈序经在岭南大学任职期间,一直住在东北区332号小洋楼里。
.gif)
东北区332号小洋楼,是陈序经就职岭大的寓所。当年因为这里花园大,学生们很喜欢在陈家聚餐、开舞会、搞活动,甚至是结婚。
复活灵魂
陈序经:一个人和一所大学
.gif)
陈序经与夫人黄素芬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伴侣。因为陈序经政务繁忙,黄素芬放弃了自己的志趣,把身心都奉献给了家庭。
这个人是陈序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一个学者,这所大学是岭南大学。
陈序经的出生成长地是文昌县,可算是地道的广东人。但是与近现代大多数广东名人一样,似乎都要经历一个走出岭南——奋斗——成名的过程,岭南成了一个输出人才的地方。与其他人不同的是,陈序经最终回到了故乡,并且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永久的轨迹。
1947年,当岭南大学董事会频频向陈序经发出邀请时,时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并没有立刻答应,虽然在这之前,他已在这所学校两度任教。也许他认为自己在南开的施展刚刚开始,也许他觉得岭南的天地太小,教育太落后,反正如果不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答应“出借”(两年),陈序经很可能不会在岭南留下太多回忆。这一“借”就是16年。
从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大校长,到1952年夏岭南大学被取消,两三年的时间,岭南大学从广东最好的学校(当时广东只有两所大学,另一所为中山大学)成为国内最完善的大学,一些院系(如医学院)已达到国内一流或最佳水平,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专家,而广州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如果考虑到这几年中国多是在政权易主、动荡不安中度过(先是解放战争,后是抗美援朝),那么,岭南大学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了。
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说起来也并不高深:一套正确的办学目标、宗旨和方略,一批一流的人才,一个高效的机制。“何为大学”?陈序经的观点是:“大学是求知与研究学问的地方”,岭大的目标:成为国内学术一流的大学。为此,他在就任校长对全校师生的第一次训词时就强调学术研究不分宗派,“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提倡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蔡元培执掌北大时的办学宗旨)的原则下,陈序经邀请到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史学家陈寅恪、数学家姜立夫,语言学家王力、古文字学家容庚、木土工程专家陶葆楷,测绘学家陈永龄,医学专家谢志光、陈国祯、陈辉真、毛文书,以及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育学家汪得亮、经济学家王正宪、法学博士端木正、生物学家廖翔华,外国文学专家杨秀珍。他们有的是陈序经的南开同事(如姜立夫),有的是他的学生(如端木正),有的是旧时相识(如陈寅恪、王力、陶葆楷),有的是他在天津时慕名去请的(如医学院的一批专家)。从某个角度说,陈序经在南开的14年(包括西南联大的8年)是为他在岭大的作为打好基础。自然,这一切得之于陈的“个人魅力”:他不经商,不做官,与政治保持距离(不入国民党)。他自己就是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和论战中表现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尊重人,“优容雅量”,以诚待人。
.gif)
.gif)
有了人,还要有钱,还要有一套精干的管理队伍。岭南大学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这些提供了保障。一手抓人,一手抓财,陈序经再次展示出他的威望和能力。在南洋和东南亚华侨中的声望使他募到大量的私人捐款(这正是岭南办学的优势),学校得以顺利渡过财政难关(而此时的中大教师正在为领不到工资而向政府抗议);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管理班子(不设副校长,而成立一个由五名教授组成的决策小组),学校得以高效运转,而“教授治校”则保证了岭大的学术风气和发展。这令人想起当年的西南联大。
天时、地利、人和,过渡的时代成全了岭南大学,成全了陈序经,但时代又仅给了他不到四年的时间。四年,相对于一个大学的成长,相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成和积累,是何其短暂!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它的工学院被合并到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农学院合并到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医学院合并到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医科大学)。经济系和法律系则被调整出去。调推后的中山大学,实际上只剩文科和理科,一批教授如王力等,被调入北京大学等院校。陈序经自己则成了中山大学一名普通教授。
陈序经立志在岭南办一所国内一流大学的愿望最终成为一个梦想。其后的陈序经虽担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不到两年),南开大学副校长,但世易时移,彼时的大学校长已风光不再。
陈序经和他苦心经营的岭南大学已成历史。但回溯历史的深处,我们仍能听到遥远的回响:岭南需要一所或数所一流的大学,岭南的落后不在经济,而在教育,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岭南完全可以办成国内一流的大学,前提条件是:一个宽松的环境,一套现代的教育体制和一个像陈序经那样的校长。
□人物访谈
女儿记忆中的父亲
卢建红(以下简称“记”)
陈渝仙(以下简称“陈”):华师附中教师,陈序经四女儿
记:作为儿女辈,你对父亲有什么印象?
陈:父亲很忙,常常是他回到家,我们都睡了。父亲全身投入到教育和学术研究上,他没有太多的时间陪我们玩和学习,家里的事,包括小孩的教育主要是由母亲来承担。父亲的关心主要体现在身教上,所以我们家是慈父严母型。
父亲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不像有的人理解的是那种很洋化西化的人,他爱国,重亲情,对长辈很孝顺。父亲的人缘也很好,上至名教授下至普通工友都有话跟父亲讲。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父亲不让别人称他“校长”,而叫他“陈先生”。
记:算起来,陈序经先生一生在岭南的时间最久,前前后后有二十多年,你怎么评价他在岭南的工作?
陈:父亲一生做的是教育工作,在岭南的工作也是主要体现在教育上,尤其是岭南大学,凝聚了父亲的心血,由于他的努力,岭大吸引了国内外一批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这些人很多后来留在了广州,执掌岭大还表现出父亲的管理才能。据说当初他刚就任时,有些教师还有怀疑,担心他的能力能否支撑起岭大,后来,父亲用实际行动消除了他们的怀疑。
还有一点就是父亲与岭大的一些同事关系一直很好,岭大解散后,父亲经常会去拜访分到华工、华农等校的老同事如汪德亮、李沛文等,每次去北京必拜访王力。
记:你的哥哥姐姐好像都从事教育工作,是否受你父亲的影响?
陈:对。我们五兄妹中,除大姐在武汉结核病防治院,大姐夫是建筑师之外,其他四兄妹和他们的爱人都在教育部门工作。二姐在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二姐夫是中学老师,哥哥是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教授,他爱人也是老师,三姐和三姐夫都是天津音乐学院教授,我和我爱人都是华南大附中的教师,现在退休在家。
父亲在指导我们选择职业时,总是先考虑教师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他和祖父一样,不愿我们去做官,做生意。他心里有一个教育情结。
记:今年恰好是你父亲诞辰100周年,社会上有些什么纪念活动吗?
陈:据我所知,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都计划有纪念活动,诸如研讨会之类;可能会在下半年。
谨以本版文字纪念为岭南文化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陈序经先生诞辰100周年。
人物词典
三妈伴读·父亲训诫
陈序经的成长中有两个人特别重要,这就是他的三妈和他的父亲。
据说小时候陈序经相当顽皮,常常逃学,在私塾读了一年多,一本《三字经》读不到四分之一,背不下来,塾师对他的父亲说:“你这孩子实在太笨,用斧头打开脑子装书进去怕也没有用,最好将来跟你做生意。”算命先生也对他的父亲说,假如他的儿子能用笔杆谋生,他就不做算命先生。而这个没读过书,不识字的三妈(陈的三叔的遗孀)却在短短的时间内使陈序经(还有他的妹妹)考到全班第一(在汪洋致远小学时),也是她力主让陈序经转入县城的学校,以免他自满。三妈的教育方法可以总结为:正面鼓励(不把陈当“笨孩子”“坏孩子”看),互相激励(将他与妹妹分在两个班,形成竞争),侧面督促(每晚亲自伴读),共同学习(她从他们学习识字乃至写信),还颇合现代教育理念呢。
陈序经的父亲是一位地道的生意人,从学徒做起,生意越做越大,做到南洋。但这位父亲又是一个仪义疏财,对读书、学习情有独钟的人物(这在中国的生意人中并不罕见)。他告诫陈“切勿想在国内做官”,“切勿想回南洋做生意”,与其做校长院长,不如靠自己的学问做个教授更稳当。在儿子取得美国博士学位后还卖掉椰子园的股份供他在法国留学。陈父的这种“文化情结”也许与其他父亲一样,是想弥补自己小时未能完成学业的遗憾,可贵的是他的见识超出常人。陈序经及他的儿女们从此与教育结缘,源头应追溯至此。
全盘西化·四场论战
陈序经与人优容雅量,谦谦君子的形象,但骨子里却有一股“好辩”、不服输的劲,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掀起四次论战。
1933年的年末,陈序经渡江到中山大学(当时在河北)做了一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两星期后(1934.1.15)演讲登载于《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版,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论战。文章中的第一句话是,“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他把关于中国文化的不同主张划为三派:“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即所谓“全盘西化”。
随后,反驳批评的文章陆续出现在同一版面,包括1934年2月2日张磬的《在文化运动战线上答陈序经博士》,里面甚至用上了“毒瓦斯烟幕弹机关枪”一类词汇,使论战充满了火药昧,两个月的时间里,出现几十篇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令人联想起16年前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与刘半农所唱‘双簧戏’引起的社会效应”(陆键东:《那一代人》)。广州这次扮演了一个论争的发源地角色,这在近现代并不多见,而最激烈的反对声音也来自于广州这一“中国人管理最西化的一个城市”(陈序经语)。一年以后,发表在《文化建设》杂志上,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人署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简称“十教授宣言”)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论战达到高峰。
从此,陈序经就与“全盘西化论者”二词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同志还有胡适、卢观伟等人。而胡适后来用了一个更折衷的词汇“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受到陈序经的批评,因为在他看来,“充分”“尽量”这些词不但含混,还很容易被折衷派和复古派拿来作护身符。
陈序经的这种“决绝”的姿态和一以贯之的观点表现出他个性中的另一面: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不畏惧权威和权贵,这在解放前是一个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在解放后却成为一道摘不下的紧箍咒,与“洋奴”、“奴化”等词连在一起。
乡村建设的论战紧随其后,论争对象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陈序经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乡村建设一途径》等文章中批驳了梁漱溟等人欲通过乡村建设使中国成为高度文明,以乡村为主体为根据社会的设想,指出在现代化的世界“以农立国”只能是一种愚妄和幻想。这可以看作是他“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深入和发展。
教育现代化·学术独立
30年代初的论争涉及两方面:教育的中国化还是现代化问题和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前者可视为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方面即他教育要彻底的现代化,所谓“中国化的教育”很容易沦为教育上的复古运动。后者与1932年广州一次教育会议提出的“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这一议案有关,支持者有当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陈序经对停办或减少文法学科持断然反对态度,在《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发表在1932年5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一文中,他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求知,为学问而研究学问”,而“职业教育的目的是求应用”,“求知固未必为了应用,然而要有所应用,则不能不求知”,废除文法学科,实是国人“只务目前的苟安与生活,而不愿做彻底的研究”的“最大的病弊”的体现。随后,论争扩展到《独立评论》等全国性报刊。
第二次教育论战的对象是胡适,1947年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提倡“学术独立”、提出在十年之内由政府指定5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作为第一等的大学培养。陈序经反对仰政府鼻息以求学术独立,认为“近年以来,一些政府人物所提倡的思想统一,以致党化教育,何尝不挂起学术独立的招牌”,指出中国大学一向集中在平、津、沪等地,不合理,指责教育部厚北京大学而薄其他大学是偏私,私立大学不一定不如国立大学,“国立大学,因可以成为政治上的党派人物所利用,而不得其公”。
陈序经的论争不是意气之争,口号之争,论争中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它理论和实践的支撑。“全盘西化论”的背后是陈序经多年孜孜研究的东西方文化系统理论,而教育方针和理论的提出又是他多年来的教育实践的结晶。故他的思考,尤其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在今天看来,仍不失警醒和指导作用。
为教育服务·为教授服务
陈序经一生中充满了悖论:他秉持不做官的信念,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做教育局长、驻外大使、教育部次长等官职,可是一生中除1931年~1934年和50年代初(1952~1956)的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官,虽然是学校的行政职务;陈序经不做生意,可是为了保证岭大教师能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按时发工资,利用开学时的学费购入物资储存,需钱用时再放卖出去保值,这不是“生意人”的行为吗?真称得上“苦心经营”;陈序经一生倡导“全盘西化”,可是自己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传统君子的形象;晚年,这位爱国、爱家乡,不喜欢吃面包奶油的人又被扣上“洋奴”、“西崽”的帽子,又岂非最大的悖论?
不变的是对教育的一种赤诚和出于公心的热情。一句“我是为教授服务的”之所以传为美谈,是因为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始终如一的行动。
据端木正回忆,陈当教务长、校长,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教学。他说,每位教授在下聘书的时候,已经是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陈说这些话,是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活档案库,他所请的教授,每个人的学术经历和特长,陈序经都能津津乐道,如数家珍。
梁宗岱教授一向在中大以“狂,怪”著称,在认识陈序经之前,陈已对梁的经历熟悉有加。50年代梁陈两家面对面,梁家没有电话,就利用陈校长的电话,所以出现校长亲自跑来充当电话传呼的情况,可谓“服务到家”。难怪据说梁宗岱在中大只佩服两个人,一是陈寅恪,一是陈序经。(卢建红)
精彩言论
若说大学改为国立,在教育行政上易于管理,这也来必是对的。大学是研究高深的智识的机关,在原则上,要想大学在学术上能够充分的发展,对于大学的研究工作,固要给予充分自由发展的机会,对于大学的行政方面,也应该给予充分自由调整的机会。……所以教育当局对于大学的行政工作,固不应处处加以干涉,而对于研究的工作,更不当加以统制。
——《论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
□个人评价
1949年6月,陈序经任职不到一年,美国岭南大学基金会负责人富伦在向基金理事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评价陈序经:“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平稳过渡,没有发生任何不满现象”;“他设法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去年没有发生超支现象,而且还有点结余以便应付以后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他重新组建了医学院,它的教职工队伍绝对被视为在中国最具实力的”;“他还加强了其他学院,特别是文学院,吸引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学者”;“他增进了校园的学术气氛,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人物传略
1903年9月1日出生于广东海南岛文昌县清澜港瑶岛村,取名序经,字怀民
1907年入私塾启蒙
1909年随父去新加坡就读
1912—1914年,还乡,先后入汪洋致远小学,文昌县模范小学就读
1915—1919年,到新加坡先后入读育英学校,道南学校,养正学校及华侨中学
1919年底回广州。行前父嘱切勿在国内做官,切勿回南洋做生意。
1929年申请入岭南大学附中被拒,同年考试直入岭大附中三年级
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两年后因不愿入基督教,转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1925年7月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授予的学士学位;8月乘船赴美伊利诺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26年获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再获该校博土学位,博士论文是《现代主权论》,该年回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1929年8月在新加坡与广东中山石岐黄素芬女士结婚,婚后即赴法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基尔大学学习
1931年回国任教于岭南大学
1934年11月15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在全国引发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战。
夏天,应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为研究教授,次年任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
1936年4月在《独立评论》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批评梁漱溟等人的“以农立国”主张,引发乡村建设运动的论战。
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
1944年8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间曾会晤爱因斯坦
1946年抗战胜利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研究所长及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1947年9月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在国内引发有关教育问题的论战
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南大学校长。延请陈寅恪、王力、姜立夫等著名学者专家到校
1952年岭南大学解散,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教授
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和广东省政协第一届常委
1962年任广州暨南大学校长
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
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2月16日患心肌梗塞在南开大学逝世。
1979年5月南开大学为其平反并开追悼、会,6月广东省政协为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2003年陈序经诞辰100周年,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将举行有关纪念活动。
本版执行/特约撰稿 卢建红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黄皓(资料图片除外)
承蒙中山大学历史系赵立彬博士惠借资料,特此致谢
上一条: [校长篇·许崇清] 中兴中大 惠泽岭南
下一条: [校长篇·钟荣光] 浪子,猛士与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