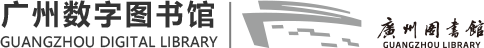对性进行压抑,更能败坏人心
欲望压抑已久的国度,人们已习惯机械而惰性的生活,哪怕有一丝小小的缺口,都会引起一阵惊涛骇浪。80年前,被视为全国最为开放的城市广州,正在热销着一本广东人张竞生博士编的书——《性史》。自此,开放和守旧再一次发生着冲突,欲望表达的底线又一次进行着移位。
事实上,1926年,张竞生的《性史》并不仅仅在广州销售得火爆,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全国各地都是热销,“一班青年男女,弄得好像饮了狂药一般”,“耳有听,听性史;目有视,视性史;口有道,道性史。”而在广州的主流媒体《广州民国日报》上,仅在1926年8月,就罕有地针对此书发表了五六篇评论。
然而,这些评论基本上都是对《性史》一边倒的批评,“能使人中魔”,“受这种电力似的撼触”,“提倡共夫共妻”——都是描绘《性史》是一本如何使人“中毒”的淫书。连其中有一篇题为《批评〈性史〉者罪人也》的评论,意思也是说:批评性史,只会是一种“炒作”,使其越炒越红,罪莫大焉。他们的态度是:即便是你讲得对,也不应当讲。
当时,张竞生担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受北大自由研究氛围的影响,在委员会讨论之后,他在北京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稿件,《性史》就是由这些稿件结集而成。其中有如小江平(金满成)《初次的性交》、一轲女士(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我的性经历》等文。前面有张竞生所作之序,每篇文章之前还有张竞生所加的按语。
张竞生在按语中发表了不少直白坦荡的议论,诸如每月夫妻之间性交几次才合适、妻子面对丈夫的调情求爱应该如何既羞涩又大胆之类。这些议论多是从他本人的道德标准、审美情趣和生活经验出发的。
不能不说,张竞生的思想远远走在了时代之前,但却未能领风气之先。他这种以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性”的著作,虽然卖断了市,但他的稿费不过二百元,也全部分给了作者,只便宜了后来十余部续书的盗版者。张竞生后来所经营的“美的书店”大胆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卖的许多是与“性”有关的书,这也成了他“向日宣淫”的一条罪证。而张竞生本人,因在法国留学,深受浪漫主义爱情观念之影响,生性风流。在《十年情场》一书中,他记述了多次他在欧洲时与外国女郎的恋爱情事,这与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国情大大相悖。张竞生也说:“《性史》之后,有人疑我是一个‘大淫虫’,荒诞淫逸。”这些评价,虽属过分,却并非空穴来风。
《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禁止和没收此书。周作人对此书态度平和,但另一位性学家潘光旦却攻击张竞生不遗余力。接着,孙传芳视为淫书,也在上海禁了此书;1926年8月,向来开放的广州也受不了这种压力,《性史》遭禁。这段时间,没有看到有什么贤达人士站出来为《性史》呼吁。
《性史》的确走得太快走得太远了。《性史》在当年是一本超级畅销书,可看《性史》的都是些什么人?是女校学生,是青年男女,是那些自制力有限的年轻人,他们都如饥似渴,如同中魔般喜欢。也许这并不是全部事实,但是,《性史》在当时很可能就像它的攻击者所说的那样,就是一本教人遐想、勾起人的生理反应的“淫书”。人们对“性”说得太少了,一旦有合法出版的畅销书谈“性”,只顾着对照着它来渲泻汹涌的欲望,根本无暇加以思考。这一点,恰好被不法书商捉住大做文章,结果通行于市的各种《性史》续篇,倒真成了诲淫诲盗之书了。种善因,结恶果,世事大抵如此。
20年代的广州“提倡解放”,是几个大城市里最后一个禁此书的(今天也是由广州率先重新出版了《张竞生全集》,包括《性史》在内),然而,报章上也只能“听取骂声一片。”鲁迅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是偏激的。今天《性史》出版不会再洛阳纸贵,因为比之更夸张更露骨的性描写的出版物比比皆是了。但是,大众的思维方式一点没有变。“做得,说不得”仍然是一条通行的定律,放眼过去都是裸女与性,然而,真正健康的性观念不仅没有建立起来,反而越走越极端。所以一方面,是惊世骇俗的性开放,另一面,却是令人发指的性无知,二者交织成今日中国光怪陆离的性景象。
近日,性学专家李银河在一次讲座上对“一夜情”、“多边恋”讨论时受到了狂热攻击:而那些反对者根本不愿进行深入讨论,而是直接抡起“道德”就当枪使。这和当年大家反对张竞生如出一辙,甚至连逻辑思路都没有变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性教育仍然远远未能完成,张竞生的主张,还远未实现。
□ 侯虹斌
不管未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会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官面前,勇敢地大声说,请看!这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写出来。我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善良忠厚、道德高尚,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 摘自张竞生在中国首译卢梭《忏悔录》
人物词典
张竞生其人
张竞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19岁考入黄埔陆军小学(编:该校虽名小学,所授课程实为高等学校课程),在那里选修了法文,认识了孙中山。辛亥革命南北和议时,他曾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与不少国民党元老人物交情不浅。不过张竞生对于政治没有什么兴趣,和议后他表示要出洋求学。1912年底赴法留学前改名张竞生,大概是受了达尔文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张竞生到法国,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0年他自法归来,先是受聘为在潮州的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推行改革:招收女生、提倡游泳。令人惊骇的是,上任伊始,他向陈炯明上书建议推行“节制生育”,被陈骂为疯子。
一年后,张竞生去职,蔡元培聘他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在北大讲授西方现代爱情、生育、性育以及有关的社会学说。他组建了“性育社”,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提倡性教育的组织。
1926年5月,张竞生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性育丛书第一集)。没料到小小一册书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上海等地一些不法书商发现《性史》非常畅销,先是大量翻印,接着又盗用张竞生之名,连续出版所谓的“《性史》续集”,达十集之多,所有恶名则由张竞生承担。他由此成了中国20世纪文化史上的有名人物,也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张竞生不得不脱离了北大,在上海与友人合资开办了“美的书店”。开张之后,生意十分兴隆,可惜,美的书店只一年多即被扼杀,张竞生的家庭也破裂。
其后,张竞生坎坎坷坷,似乎已经壮志消歇,几番波折之后,回到饶平,做了一些组织修筑公路、开办苗圃之类的工作,逐渐下降为家乡一个地区性的人物了。
“文革”中,他饱受冲击。1970年,张竞生脑溢血去世,终年82岁。
.jpg)
张竞生,1952年于广州南方大学。
.jpg)
1922年,美国宣传节育的专家山格夫人应邀到北京大学讲演,胡适(左)任翻译,张竞生(右)陪同,中为山格夫人。
.jpg)
张竞生在上海开设美的书店,专售性知识方面的书,雇员也全是年轻漂亮的女性。叶卓侠 摄于1928年
.jpg)
《性史》一问世,就深受女青年的喜爱。 本版漫画 乌有作坊
.jpg)
1926年夏天,《性史》在广州热销。
.jpg)
新旧人物争对《性史》内容进行评论。
.jpg)
1926年8月,广州查禁了《性史》。
旧闻回眸[一]
《性史》热销广州
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性福”的生活。永恒的山脉向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蜿蜒绵亘。知识的小溪沿着深邃破败的溪谷缓缓地流着。它发源于昔日的荒山。它消失在未来的沼泽。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做张竞生的广东人,编了一本叫《性史》的小册子,这个信息屏蔽山谷里的村民才发现,在人们习惯和视野之外,还有一个更玄妙的世界。
诲淫的《性史》
据1926年8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 文/怪 近来广州市内有一种看书的流行病。无论大学生小学生,无论何时何地,均手不释卷。你道他们所看的是什么书呢?他们所看的是北京鼎鼎大名的教授张竞生所著的《性史》。《性史》内所载以一舸女士那篇及江平那篇为最卓绝。故近日学生中说起董二嫂的故事,无有不晓。秽亵远教之语,和盘托出,竟值得他们津津有味。
现在广州市内的《性史》,统计已有五千余本(国光售出二千本,光东一千本,丁卜一千五百本,民智五百本。)现闻昌兴街丁卜书店更由上海订购了五千本。每本定价四角,不日书到。决定每本以八角为代价,书尚未到,已为各校学生定尽。计此项《性史》定购者以城北及城东某两女校学生为最多。统共为若辈,定去者已达三千本。此后正可实地研究性的问题呢!
某报何如先生,谓照这样说,天地间无所谓禁书,无所谓淫书了。《玉蒲团》、《金瓶梅》,不幸竟登上于禁书,惟《性史》公开买卖,何其有幸与不幸耶。上海方面,已为孙传芳目为诲淫,下令警厅严禁。本市提倡解放,想不至于如上海一样禁绝吧?
我也说《性史》
据1926年8月20日广州民国日报 文/杨萌 自从这册《性史》出世以后,因为惹起许多批评家的热烈赞扬和剧烈的排斥,于是这种很平常的出版物就随着赞扬和排斥的声浪而形成了一种可崇拜可恐怖的奇怪的东西似的。我也受着好奇心的冲动,走去书店买一册来看。
回到旅店后,就朝这闷葫芦似的《性史》细心看去,果然,《性史》的编者张竞生博士的序言内,将《性史》的研究如何重要,这册书的价值如何高贵,如流水一般地一一提示出来。最后还再三慎重地告诉读者,要有对于此书——《性史》不是淫书的信仰。读到此处,真令我赞美不绝了,殊不知看到了下篇,使我狂叫起来。
原来这册《性史》的材料是由几个青年男女将他们性欲中的经过事实,“现身说法”地写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如一舸女士《我的性经历》,江平君的《初次的性交》两篇内,将各种交媾的方式,交媾前后的方法,交媾时的兴趣等……五花八门,兴情的、肉麻的、描写齐全。我本是一个未婚的青年,可是看到了这些地方,如中了什么魔似的使我的精神上发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变化,遂至身不自主地心火熊熊甚至于不能自已。啊,《性史》的魔力啊。
亲爱的青年男女们,男女之者间的性研究我们固然不能反对的,但是,这种狎亵的诲淫的出版物万不可拿它来做正当的研究,如果不然,在一般血气未定的——尤其是未婚的青年男女一受这种电力似的撼触,便会心旌摇摇地轻于一试——至少也会使生活上、精神上感受不安的。
诲淫的“春宫”已经禁止出售了,我希望把这类的《性史》禁止出售吧。
旧闻回眸[二]
看《性史》的传染病
据1926年8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 作者不详 自从性欲博士所编的《性史》来到广州之后,一班青年男女,弄得好像饮了狂药一般,说一句真实的话,确是“耳有听,听性史。目有视,视性史。口有道,道性史”了。《性史》的魔力真是大得很哩。但是看过的人,有什么好处没有,我却不用头脑去批评了。
城北的某女校,在市内是数一数二的学校,有一位密斯A,在那里肄业,她有一位妹妹,总得十二岁,这天,她在人家那里拿了一本书回来。她本来还没有看出的程度,但是她看见封面那一双裸体人儿,却喜欢异常,就多了一件像钩似的物事,尤觉奇怪,所以就带回家去。想请教姐姐密斯A,密斯A看了,欢喜得如同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一般,立刻精神上就觉得有点异感,没半个钟头就全本看完了。
到了第二天,密斯A来了几个同事,看见案头有这样宝贝的书,就你攘我夺地争着来看,后来经密斯A的调停,还是以抓阄来判决,结果是二年纪时常占首座的那位密斯抓着第一了,自然很欢喜,落选的就很懊丧。
可以理解,为何今天永汉路一带书坊里的《性史》,竟为之一空了吧。
看了《性史》的批评
据1926年8月广州民国日报 文/俞雄飞 我以为性本有研究的价值,如果出之纯正,也足以创古今的奇论,发圣人所不言,为新潮流所不可少的生理常识,我对《性史》有无穷的奢望。孰料阅读,掷书三叹曰,是无价值的出版也。
江平就食于董二哥,是一饭之恩,古人不忘;董二哥外出,对于其妻,应负照料之责,否则,避嫌搬出也可。天下多美妇人,何必与有夫之妇通奸?物各有主,如果不是我的,虽一毫而莫取,何况夺人之妻?而纵一已之淫乐,良心何在?……江平干此勾当,公然作为资料,跻身于衣冠之列,吾辈羞与为伍也。
其他如一舸女士,既与夫的志趣不同,应提出正式离婚,却暗私他人,而屈身于两人之间。此不过为贪图新鲜,交往不久,断无纯正的真爱情。一夫不能满足我之所欲,则十夫可也,与人类性的真面目,已失诸千里矣。我敢大声疾呼,该《性史》实含鼓吹公夫公妻的意味,行于国中,将沦于禽兽之邦。政府应当出一纸禁令,就如农夫除草,令其不蔓延也。
批评《性史》者罪人也
据1926年8月广州民国日报 文/北洌 许多批评家说,《性史》是一本淫书,不应给年轻人看。这本来是爱护青年的一点好意思。但我以为人们总带点好奇性。这么一来,不啻给他们一个暗示说:“青年们啊,你们想满足你们的好奇心,快快买本《性史》看看罢。”可不正是“爱之反足以之害”吗?
如果承认因这次报纸批评《性史》宜禁方才禁,那么警察方面也逃不了失察的地方。且在既宣布之后,未禁卖以前,不啻予买卖以一发财之机会。未禁卖以前数千册《性史》早已散布全市了。换言之,推销《性史》者可说是反对《性史》之批评家。因为有《性史》的批评,人们方才知道《性史》是一本禁书。尤其是前天杨荫君《我也说〈性史〉》一文的轻描淡写,像这样的推波助澜,其罪更浮于原作者之上。
如果《性史》有性教育上的价值,那么,如医生、心理学教授、与性教育的训育者,不当一概禁买。如果的确是一本淫秽的书,非但要以后完全禁绝,连以前所卖的数千册,也要一一追回销毁。
名人评说
至于张竞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要在25世纪。
——鲁迅
张竞生在校外出版了一种《性史》,其内容猥亵,很遭物议。我虽也认为给社会的影响不良,然却谅解其人似与下流胡闹者有别。
——梁漱溟
编《性史》的张竞生,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和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目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
——李敖
《性史》选登
譬如有夫对妻说∶我看今夜你怎样对付我呢,女子此时不免脸一红,但此时女子应当向其夫热热湿湿地亲一深吻,并应说∶恐怕你连战皆败啦!此时情况何等美丽,周围空气又何等热烈;若女子面一红就走避了,则变成何等寂寞无聊了。故只知羞涩而不敢大胆,与只知大胆毫无羞涩的女子同样欠缺自然的美感。
专家访谈
张竞生没有失败
被访人:江晓原,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博导、人文学院院长。
记者:现在重评张竞生,你认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江晓原:这些年已经给张竞生平反了,他的家乡饶平早就开始纪念他了,《性史》也在1998年由广州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对张竞生的基本评价就是:他是“中国性学探索的先驱人物”。很少人再去批判他了。
记者:他是现代中国性学第一人吗?当时还有谁在研究性学?
江晓原:很难说张竞生就是独一无二的。当时激烈抨击他的潘光旦自身也是性学研究者,译介了一些西方性学著作(如霭理斯《性心理学》),还在中国古代书中搜集资料。另外,《性史》的出版是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周作人、顾颉刚、刘半农等人都参与了。《性史》并不是张竞生一个人的主张,像周作人,也十分赞同对色情歌谣的收集。但最后,张竞生成了受害者,不法书商编出了色情的《性史》续篇,却让张竞生背上恶名。
记者:《性史》是一本怎么样的书?
江晓原:《性史》是一个社会学的调查研究,里面集中了多个个案采访。我认为这只是性社会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意义当然有,也不宜提得太高。
记者:张竞生是否失败了?这是因为他太超前了吗?今天他的思想是否仍然超前?
江晓原:我并不认为张竞生是失败的,因为历史最终承认了他。只是他对人心之坏没有一个准确的估计,《性史》的出版对他造成了伤害。这也与他观念超前有关。张竞生很多关于性与情感的观念、言论,在今天合法出版物中都随处可见了,但大家都无异议。他的书再版也没有什么反对声音。这说明我们现在对这方面的心理承受力已经很强了。
记者:今天,研究性学是否仍受到贬斥?
江晓原:我不觉得。我研究性学已20多年了,是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而且我本来就是天文学者,跨行而为,按理我应该有更大压力,但并没有。当然,也不排除会有一些人在研究或探讨性学的时候有顾虑。不过,这个社会总有人保守、有人开放。性学研究者接触的事物较多,跟公众比起来,当然会更宽容一些,有些读者对性学者的观念不能接受也不足为奇。那些批评张竞生的人的态度一般都是:即使你讲得对,也不应该讲。我认为,对性进行压抑,更能败坏人心。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侯虹斌
实习记者 熊雅芳
本版图片资料来自《张竞生传》一书
本专题由本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
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提供馆藏报纸。
上一条: 大时代背景下女招待之命运
下一条: 把汽车叫“市虎”的年代